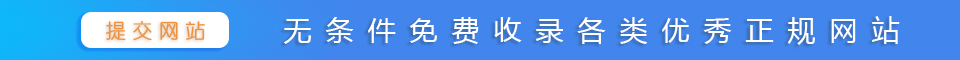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二维码收付款功用的始终遍及,行为人将商店用于收款的二维码偷换老自己的二维码,经过顾客付款,将本应属于店主的款项据为己有的案件时有发作。针对这种行为的定性,通常上有不同观念,通常中不同法院的认定也不齐全相反。本文将剖析争议发生的缘由和司法通常中认定的现状,并论证笔者关于该行为合乎诈骗罪之形成要件的观念。
一、争议发生之缘由
关于该行为的定性,主要存在偷盗罪与诈骗罪的争议。由于我国刑法依照不同的行为形式,对取得型财富立功规则了不同的罪名,所以对行为手腕自身的钻研关于认定财富立功的详细罪名具备重要意义。
在偷换二维码诱使顾客向自己付款的案件中,行为人获取商家应收款项的环节借助了顾客付款这一行为,行为人取得钱款时间点和形式具备不凡性,因此对这种行为的定性或者由于对抗功对象以及行为手腕的不同了解而造成出现不同观念。
二、司法通常认定之现状
笔者经过检索,发现目前颁布在裁判文书网上的相似案例中,大局部法院将该行为认定为偷盗罪,但少数裁决中都没有明白论述理由,而是直接认定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因此成立偷盗罪。裁判理由论证较为充沛的有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1刑初1070号刑事裁决书,认定该行为形成偷盗罪,以及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902刑初203号刑事裁决书,认定该行为形成诈骗罪,这充沛表现了该行为的定性疑问在通常中也有较大争议。
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裁决以为该行为形成偷盗罪,理由是:首先,原告人驳回秘密手腕,掉换(笼罩)商家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支付给商家的款项,合乎偷盗罪的客观形成要件。秘密掉换二维码是其获取财物的主要。其次,商家向顾客交付货物后,商家的财富权益未然处于确定、可控形态,顾客必需立刻支付平等价款。微信收款二维码可看作是商家的收银箱,顾客扫描商家的二维码即是向商家的收银箱付款。原告人秘密掉换(笼罩)二维码即是秘密用自己的收银箱换掉商家的收银箱,使得顾客交付的款项落入自己的收银箱,从而占为己有。第三,原告人并没有对商家或顾客实施虚拟理想或瞒哄假相的行为,不能认定商家或顾客客观上受骗。所谓“诈骗”,即有人“使诈”、有人“受骗”。本案原告人与商家或顾客没有任何联络,包含当面及隔空(网络电信)接触,除了掉换二维码外,原告人对商家及顾客的付款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商家让顾客扫描支付,正是原告人驳回秘密手腕的结果,使得商家没有发现二维码已被掉包,而非客观上被迫向原告人或原告人的二维码交付财物。顾客基于商家的指令,当面向商家提供的二维码转账付款,其结果由商家承当,不存在顾客受原告人诈骗的情景。顾客不是受骗者,也不是受益者,商家是受益者,但不是受骗者。综上,原告人邹某某的行为不合乎诈骗罪的客观形成要件,其以秘密手腕掉换商家二维码获取财物的行为,合乎偷盗罪的客观形成要件,应当以偷盗罪清查其刑事责任。
与之唇枪舌剑,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以为该行为形成诈骗罪,理由是:偷盗,是指违犯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或财富性利益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就本案而言,其一,就酒店或商铺的商品而言,并不是原告人违犯商户的意志直接或经过商户将商品转移给顾客占有,而是商户基于意识失误将商品转移给顾客占有,所以原告人不成立对商品的偷盗。其二,就顾客对银行享有的债务而言,也不是原告人违犯顾客意志直接或经过顾客将债务转移给自己占有,而是顾客基于意识失误将其对银行享有的债务转移给原告人占有。因此,原告人的行为不成立对顾客债务的偷盗。其三,就商户对顾客的货款申请权来说,原告人并没有使之发生任何转移。换言之,即使商户丢失了货款申请权,但该申请权既没有转移给顾客,也没有转移给原告人,因此原告人对此无法能存在偷盗。综上,本案不定偷盗罪。
本案合乎诈骗罪的形成要件,只是其与传统诈骗罪的结构有所不同,其结构为:原告人实施诈骗行为—受骗人发生或继续维持意识失误—受骗人基于意识失误奖励或交付自己的财富—原告人取得或使第三者取得财富—被害人遭受财富损失。这种结构与传统诈骗罪结构不同的是,受骗人与被害人并非同一。本案受骗人是顾客,被害人是商户,而受骗人具备向被害人转移或奖励财富的任务,并且以实行任务为目标,依照被害人批示的形式或以法律、买卖习气认可的形式转移奖励自己的财富,只管存在意识失误却不存在民法上的过失,但被害人没有取得财富,并且丢失了要求受骗人再次转移或奖励自己财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顾客由于购置商品或取得服务具备向商户支付货款的任务;顾客依据商户的批示扫二维码用以支付商品对价,只管无心识失误,但并不存在民法上的过失,商户却遭受了财富损失。在这种状况下,顾客奖励自己银行债务的行为,就直接形成了商户的财富损失。因此,本案应定诈骗罪。
经过上述两个有代表性且说理较为充沛的裁决可知,关于该行为如何定性,在通常中也存在明白的不同的两种观念,且各自都较为充沛的论述了理由。笔者以为,该行为合乎普通诈骗的形成要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而不应认定为偷盗罪。
三、诈骗罪之主张及外部争议评析
笔者以为本案行为人形成诈骗罪。依据相干刑法通常,诈骗罪的行为形式为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使具备财富奖励权限的人堕入意识失误并基于意识失误奖励财富,行为人获取财富,被害人遭受财富损失。本案中,行为人的立功对象是店主应得的相应商品的款项,被害人是商家。行为人瞒哄了二维码被改换的假相,实施了向顾客展现被偷换的二维码并要求顾客付款的诈骗行为,使顾客堕入意识失误并基于意识失误奖励自己的财富,这一奖励行为造成被害人商家遭受财富损失(相应商品的应收价款),齐全合乎诈骗罪的行为形式。
在上述诈骗罪的行为形式中,本案或者存在的不懂是顾客能否堕入了意识失误。有观念以为,本案中的顾客没有堕入意识失误,顾客并不负有审查二维码的任务,且其扫码付款的行为自身曾经实行了付款任务,其对付款的性质并未发作失误意识;亦有观念以为,本案中的顾客只是对奖励性质发生了意识失误,而并未发生奖励缘由的意识失误,故即使存在一定的意识失误也不成立诈骗罪。笔者以为,只需财富奖励人堕入了“奖励财富”的意识失误即属于诈骗罪中的意识失误。之所以刑法通常上必需对意识失误作出一定的限度,不能泛指任何失误,是由于必需一定意识失误与诈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意识失误的发生或维持是基于诈骗行为。至于性质失误能否属于意识失误也不能一律而论,而是要详细剖析这种失误能否造成了缘由失误,若扫除这个失误,财富奖励人能否依然会实施奖励行为。详细到本案中,顾客是由于店主具备基于买卖关系收取款项的权益,才向店主这个特定的对象付款。换言之,假设顾客知道收款方不是店主,顾客则不会付款,这说明意识失误造成了奖励行为的发作。而以至顾客堕入意识失误,以为收款方是店主的缘由,恰好是行为人瞒哄二维码已被偷换的诈骗行为,故合乎诈骗罪的成立条件。

在主张成立诈骗罪的观念中,有观念以为本案属于三角诈骗。笔者以为这种观念值得切磋。所谓三角诈骗,只不过是诈骗罪中的一种较为不凡的情景,其指堕入意识失误并奖励财富的人并非被害人的场所。一方面,典型的三角诈骗中,财富奖励人所奖励的财富必需是被害人的财富,而本案中的顾客奖励的是自己的财富,因此不属于三角诈骗;另一方面,“三角诈骗”的提出实践上是为了明白被害人与财富奖励人的不同,只是诈骗罪中的一种不凡情景。由于立法上没有规则诈骗罪的成立必需以堕入意识失误的人自己交付财物为前提,因此只需一定堕入意识失误与奖励财富之间,以及奖励行为与财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的三角诈骗当然满足诈骗罪的成立条件。故笔者以为,在认定诈骗罪时,没有必要刻意辨别被害人与财富奖励人能否同一。
另一种观念以为本案的立功对象是店主享有的债务,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造成店主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奖励了自己的债务,因此成立诈骗罪。笔者以为这种观念有一定的情理,但在解释“店主对债务虚施了奖励行为”这一要件时必需驳回途分意思不要说,并同时一定不作为和容忍型的奖励行为,这或者存无通常上的阻碍。固然,诈骗罪中的奖励行为不限于民法上的奖励行为,而是包含所有作为、不作为和容忍行为,但最主要的疑问是案中的店主不存在奖励意思,其存在的意识失误是误以为债务曾经行使,而并没有奖励债务的意思,在这种状况下店主无法能存在不行使债务的不作为行为。正如针对奖励意思不要说的批判意见所指出的那样,假设不要求有奖励意思,就或者否定不作为与容忍类型的奖励行为。上述观念将奖励意思不要说与狭义的奖励行为两种学说并存,或者存在一定的通常阻碍。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该行为齐全合乎普通诈骗罪的结构,可以直接依据刑法的规则认定为诈骗罪。
四、偷盗罪之反驳
以为本案形成偷盗罪的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观念以为立功对象是债务,行为人经过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偷盗了店主的债务;一种观念以为立功对象是款项,行为人用鲜为人知的方法偷换二维码,秘密窃取本应属于店主的钱款。
针对第一种观念,债务不能作为偷盗罪的立功对象。债务是申请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益,属于财富上的申请权,无法被窃取。从民法的规则来看,造成债务覆灭的情景包含清偿、抵销、提存、罢黜和混淆,因此偷盗行为无法使债务灭失。详细到本案,只管行为人偷换了二维码,商店依然有权益要求顾客支付相应的对价,债务自身并未被偷盗。所以即使以为因偷换二维码的行为造成了店主的财富损失而形成偷盗罪,立功对象也只能是详细款项而非债务。
第二种观念过火强调秘密与骗取的区别,且疏忽了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与店主遭受财富损失之间染指的顾客付款的行为。笔者以为,一方面,秘密窃取和骗取并非本案辨别偷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理由是诈骗罪诈骗行为中的瞒哄假相的行为也造成了店主对二维码改换的理想不知情,秘密窃取指的是取得财物的手腕,而鲜为人知则是瞒哄假相的结果,故不能简略地以不为店主所知推出秘密窃取的论断。况且,笔者以为偷盗罪的外围是合法转移占有,秘密性并非偷盗罪的必备要件,用手腕行为能否具备秘密性作为偷盗罪和诈骗罪的辨别规范是对偷盗罪实质的曲解。另一方面,本案行为人实施的改换二维码的行为不会对店主的财富形成任何损害,其取得财富、店主遭受财富损失的结果是经过顾客的付款行为成功的,而这正是偷盗罪与诈骗罪状为形式的实质区别。偷盗罪中普通由行为人直接取得被害人的财富(直接正犯的场所除外),诈骗罪中行为人无法经过诈骗行为直接取得财富并造成被害人的财富损失,必需借助一个媒介,在本案中即是顾客付款的行为,并且这一行为才与法益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最理想紧迫的咨询。正是基于这样的区别,偷盗罪被以为属于攫取型取得财物的财富立功,而诈骗罪属于交付型取得财物的财富立功。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以为,本案行为人实施偷换二维码的诈骗行为,经过顾客付款的买卖行为取得店主应收款项,故成立交付型取得财物中的财富立功中的诈骗罪,而不形成属于攫取型取得财物的财富立功中的偷盗罪。
注释:
1参见(2017)闽0581刑初1070号刑事裁决书
2参见(2019)闽0902刑初203号刑事裁决书